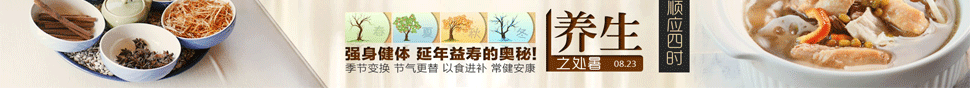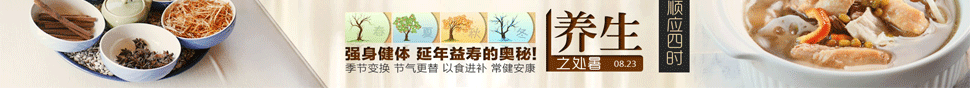周末,朋友叫袁小猫去龙首原吃涮肉,其实本来不想去,上周就休息一天,五一去神木来回的疲惫劲儿还没缓过来,加上又上了几天班,整个人都像被掏空了。但是,任谁也阻挡不了一个吃货对肉的向往啊!一锅涮肉镇个楼查了一下导航,从袁小猫家门口刚好有一辆公交车路可以直达,于是就晃晃悠悠过去了。袁小猫这些年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南郊及浐灞活动较多,对北边其实不是很熟悉。走到龙首原的时候觉得还挺新鲜,所以也是边走边看。河边的“蒙古村“龙首北路还挺宽敞的,路边卖水果的特别多,很便宜。按导航到那个涮肉店门口的时候,袁小猫忽然看见路对面有个石碑,上面写着三个字“马泘沱”。来都来了,对面这个看起来挺古老的石碑得去看看,毕竟我们大西安文物古迹太多了,处处都有故事。转到对面发现这个石碑是年立起来的,对着街道那边是袁小猫看到的马泘沱三个字,后面是斑驳的村志。袁小猫使劲儿使劲儿地辨认,才恍恍惚惚辨别出一些字迹,大意是该村始于元代,原来叫马家滹泘,泘沱源于蒙古语,是水边的村寨意思。相传,当年村边水草肥沃丰美,水中可见蚌壳,“依渭水,南望长安,宫阙环绕,龙脉宝地。”几经战乱,到民国年间,该村鼎盛时期已过,人口只剩数百人,主要以农耕为主。马泘沱村的石碑石碑后面记载了这个村的简单历史此前有有人采访过长安大学社会学教授戴生岐,他说古时八水绕长安,有水的地方很多,泘沱一词来源蒙语,而蒙古人逐水草而居,这些泘沱村的村民,很有可能就是蒙古人的后裔。这么说来,这个马泘沱村村民有可能是蒙古人的后代啊!站在这里,袁小猫抬头望去,马泘沱村四个大字在苍翠的绿树掩映下依然耀眼,时过境迁,曾经的河流早已不再,村民们也因为拆迁都搬走了,剩下只有这个能依稀看得见历史的村名。树荫背后的马泘沱村河对岸的一口锅一切都好像是冥冥之中的缘分,今天在这里袁小猫遇见了曾经的蒙古村落,而要去吃的是京味涮锅,围着一口锅,大家伙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历史的村落虽然会远离,但是味觉的记忆总是不离不弃。马滹沱村对面的京味涮肉馆在袁小猫的印象里,铜锅涮肉是满清电视剧里暖冬必备菜品,就是来源于那遥远的大草原。在老北京人的生活里,呼呼的北风刮着,一大家子围坐一锅,涮肉涮菜,升腾的热气在小屋里弥漫,清淡中透着浓郁的香。这家叫朋来聚的馆子是在二楼,拾阶而上,内有乾坤。二楼整个大厅人头攒动,有卡座、有带着帘子的包间,朋友们选择了靠窗的8人方桌。铜锅开了花生米就着老北京铜锅涮肉的锅底讲究“清水一盏,葱姜二三”,几片生姜、几个葱段,就是所有的锅底内容。眼见着服务员提着矿泉水桶咕咚咕咚往那铜锅里倒,然后很随意地往里面撒进去。几个葱段、几个大枣、几粒枸杞,果真泾渭分明啊!这与川味火锅的麻辣江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锅底很清京味涮肉,吃的就是个清爽大家都知道川味火锅的麻辣鲜香,那在江湖上是声名远播的。但是京味铜锅涮肉的至纯至真也是受到了很多老饕的重度惜爱。清淡纯净的锅底就像一面镜子,所有食材必须经得起锅底的考验,尤其是羊肉,当然还有牛肉。对于真正的吃家来说,吃涮锅,羊肉一定的是要手切的,如此手切的羊肉没有血水、没有异味,可以立盘;有些用机器切出来的羊肉,由于长时间冷冻,已经破坏了羊肉内部的细胞壁,解冻之后的肉质纤维被破坏了,原有的韧性弹性损失,别说涮烫,筷子一拨拉有时候都会断开,那样的肉看着都没有食欲,又谈何吃?那天我们吃的无论是肥牛还是肥羊,肉质纹理紧凑,色泽自然,薄厚适度。袁小猫一筷子夹好几片放进锅里,只不过几秒,鲜嫩的肉卷从眼馋变成了口馋,捞起来蘸一下店家秘制的料碗(蘸料宜轻轻点水,不可全部裹进去哦,不然味道过重),送进嘴巴。数秒间,诱人的羊肉出锅了对了,忘记说那个料碗了。当然了,老北京铜锅涮肉的蘸料,最灵魂的自然是芝麻酱,而其他的比如豆腐乳、酱油、香油、虾油卤等也是必不可少,每一样都能让料碗的口感层次更加丰富。当然,油炸辣椒实在是太完美了!袁小猫不仅往料碗里放,而且直接夹起来当菜吃,咱可是真正爱吃辣的陕西人啊!糖蒜不能很少麻酱料碗里的腐乳很诱人那一顿,我们八个人吃了6盘肉,真是太能吃了!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凉菜、热菜若干(但吃得不多,都顾着涮肉吃了),反而最后的一个炸油馍,竟然也成了抢手货。袁小猫尝了一个,酥软脆香,是裹了鸡蛋液后油炸的,十分可口。#美好生活家#这个羊血很不错金黄的炸油馍,很好吃没有轰轰烈烈的麻辣江湖,却在轻轻浅浅的一口铜锅里,感受到了平凡生活的美好滋味。对面的马泘沱三个字依然静默,那个不远千里来到河边的村落早已物是人非,但是,这一口个性鲜明的京味涮肉,依然饱含深情,传递着千百年前棱角分明的好味道,你吃了吗?额是袁小猫,一个爱吃爱喝爱你的陕西女子!
本文编辑:佚名
转载请注明出地址
http://www.nvzhenzia.com/nzzpz/1406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