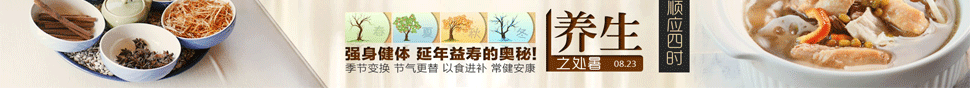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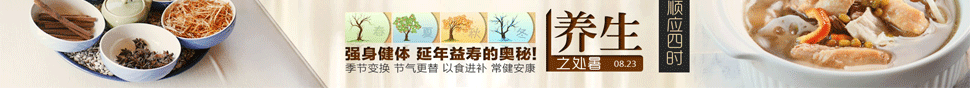
佛王村历代相传有戏班,相传约在民国初年间,有一聂家大戏班,为京剧班。其演绎水平较高,而远近闻名,班中有好几位出名的角色,有“自江的领子(唢呐),克乾的锣、肇云就是活关爷”的流传故事,自江是戏班的司鼓,练就一手吹拉唱的绝活,吹奏,唢呐,更是技艺高超,不仅用嘴吹,而且还能用鼻子吹,还会把哨子含在嘴里吹出各种各样的鸟鸣声。克乾打锣还兼管舞台的布置,道具的摆放。一次,演出的间隙他在舞台正中摆放桌椅,而开场的锣鼓响了,他急中生智,把手中的锣锤顺手一甩,锣锤正好击中挂在锣架上的铜锣中央,“咣”,正好在需要锣声的点子上,他随即跑过去捡起锣锤击打了起来,从此就有了“聂一锤”的名号。
一次戏班到潍县(现在潍坊)演出,第一场由肇云出演三国戏千里走单骑,肇云因下午喝了几杯酒,朦朦胧胧有些睡意,而他的跟包的不在身旁,肇云靠坐在戏服箱上打盹,忽然剧场响起了“急急风”的锣声,饰演周仓的演员催了他一声,自己就一溜跟头翻了出去,可他的脸谱未画,急中生智用墨笔吊了眉,披上战袍就出场了,他走到台口亮相,台下一片哗然,嘘声不断,“怎么来了一个白脸的,关公变曹操了”肇云一听,酒意全消,好在他练过气功,会运气,忙把袍袖把脸一遮,运气硬是把脸憋成了红色,袍袖一放,白脸变成了红脸,立时台下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和叫好声。”白脸变成了红脸,真是活关爷呀”从此肇云就有了“活关爷”之称,而聂家大戏班在潍坊连演了十天,场场爆满。
还有一年,五月六月连月干旱,旱的庄稼快要枯死了,村中长者带领村民在大庙神灵前许愿、祈雨,若天降大雨,庄稼获得丰收,就唱戏庆贺,不几天果真下了大雨,保住了庄稼,又接连几场雨,不大不小,庄稼长势喜人,丰收在望,村内长者便张罗唱戏还愿,因看久了自己戏班的戏,而想换换口味,就到博兴请了一个较有名气的京剧班前来,但他们提的条件很高,每天要吃宴席,住宿要每人一张床,一顶蚊帐,还要有仆人伺候。在当时就算条件高的了,村里的长者与佛王村聂家戏大班商量了应对的办法,答应了他们的条件。在戏班来的那天,戏班的当家老生与青衣便装成了拾柴草的庄稼人,在小清河西岸、来道口的路边上的荒地里,拉着大耙等候要来的戏班。
晌午时分请的戏班坐着大马车来到了村头,这时他们二人口念着“锣鼓经”唱着胡琴伴奏,一唱一念的唱起了“四郎探母”中的“坐宫”一折,高亢圆润的声音传到了被请来的班主和演员的耳中,他们细细听来,唱得是字正腔圆,有板有眼,于是他们停下车来,把这两人叫到跟前,问他们唱的戏是跟谁学的,他俩说是村里戏班排练时听来的“耳弯言”,可明白人一听就知道这二人唱功很好,根本不是什么“耳弯言”,看来这个村的戏不好唱、要注意所开的条件不能太高,要改变原来的条件,进村后,村里把他们安排在了聂氏家庙中,也没有床,也没有蚊帐,而是打的地铺,并给了他们些艾蒿搓的草绳熏蚊子,就这样他们非常卖力的连唱了三天,最后聂家大戏班的几个名角在他们的要求下,也和他们一起合演了几场戏,而博得了他们的赞誉。
自从吕剧在广饶县传播以后,村里的一些爱好者也学唱起来。年前后,他们利用冬季农间组织学唱,当时有聂绍胜、聂在邦、聂绍油、大蓉、聂兆桌、聂兆南、聂绍庆等人组织了戏班,逢年过节在村内搭台唱戏,周围的村庄都来观看。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广饶全境解放更是给他们带来了好时机。解放初期一直到年的这几年中,村中吕剧发展较快且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创出了“老四平”“佛王四平”等腔调,先后组成了东西两个戏班,村东头由聂绍杰、聂绍满、聂作典、聂作强、王玉坦、聂在木、聂士松等人。村西头有聂绍胜、聂绍庆、聂绍功、聂在邦、聂在营、聂充增、聂兆良、聂绍会、聂在祥、聂作安、聂在典等人。两个班既单唱又合作,演出的主要剧目有:大戏铡美案、彩楼记,小戏有:小姑贤、王小赶脚、双生赶船、洞宾戏牡丹、丁松扫雪、黄氏女游阴、老少换妻、王定保借当等等。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